谁提出的“打倒孔家店”?
所属学科:全部学科发布时间:2015/10/26 10:08:41来源:社会科学报
关注"壹学者"微信服务号(my1xuezhe)了解更多学术动态
在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中,系统、深入地考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诞生与衍化问题,或许是学界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的有效途径,可以避免一些因话语的不可通约性而起的无谓纷争再度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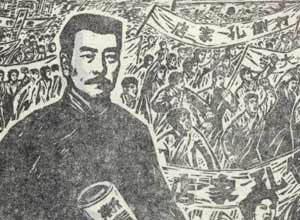
符号,话语的洪流
从去年至今,“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及类似词组时时现诸平面与网络媒体,也频频现诸展览、纪录片、征文活动乃至《胡适自述》等书籍的腰封。“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是中国学界与出版界的热门词与关键词之一。各种背景、各种立场的人们针对“新文化运动”的 “接着说”、“正着说”或“反着说”,客观上都会汇入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的话语洪流中,有的甚至可能成为新文化运动阐释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其本已宏富而繁杂的话语殿堂添砖加瓦。
面对这些反思百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我们或许有必要从话语梳理的角度重新重视“如何继承,怎样反思”的问题。因为既有阐释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关键概念极可能继续出现,一旦它们不具有确定的内涵与外延,那么,我们表面上异常热闹的讨论,乃至针对诸如新/旧、现代/传统、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承续/断裂等问题而出现的争论,就可能仍然缺乏足够的有效性。“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化研究,其中也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基本概念的混乱”。王富仁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正名”问题》中的这一提醒,在 20年后的今天依然有醍醐灌顶之效。事实是,近年来诸多对现代性、科学、封建、国学等概念或曰知识的考掘,已经局部更新了我们的“常识”,让我们透过那些习焉不察的词语的前世今生,窥见了思想演进的复杂面相,使得我们在小心翼翼的阐释与运用中不断拂去那些层叠起来的文化尘埃,从而增加了有效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在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中,反思、考索那些话语中的关键词或曰概念本身的诞生与衍化中的意蕴变迁,或许就是一条值得重视的返本开新之路。
最基本的问题最困惑
“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阐释话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组。这个涉及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孔子、儒学以及孔教之关系的关键概念,不仅屡屡被赞成或反对新文化运动者提及,而且常常被论者言之凿凿地指认为五四时期的“口号”。在相关论著或论文中,提及“打倒孔家店”或程度不同地展开对它的论述者比比皆是,将“打倒孔家店”作为小标题者也屡屡可见;在《中华读书报》、《人民日报》以及凤凰网、新浪网等媒体上发表的报道或杂感中,“打倒孔家店”也是一个被多次提及的词汇;在百科全书、辞典或者普及性著作中,有关“孔家店”、“打倒孔家店”的条目或解释也已屡见不鲜。
让人疑惑的是,既然“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时期的口号,就理应有一个提出者。然而在那些言说中,有认为该口号是由胡适提出的,有认为该口号是由吴虞提出的,还有的认为该口号是李大钊、鲁迅、易白沙或陈独秀等新文化先驱提出的,或者只笼统地指认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民初知识分子提出了这一口号,而不具体落实到某个人。
让人疑惑的还在于,这一理应有明确所指的口号,在那些言说中,其所指却不断滑动。比如“孔家店”一词,径直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者有之,将其与封建、专制直接对等者有之,将其与孔子的思想学说、儒家思想、儒家意识形态、孔教及其徒子徒孙联系起来的也有之。显然,封建与专制不可直接对等;孔子的思想学说、儒家思想、儒家意识形态与孔教之间,并非可以完全通约;孔家店与传统文化的范畴,也并不完全等同。
更让人疑惑的是,从1930年代至1970年代末的近五十年中,论者们不仅对这一含混的“口号”深信不疑,而且循此对“打孔家店”或“打倒孔家店”行为本身,对陈独秀、胡适、吴虞、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现代文化作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即便在1980年代已有学人质疑其真实性、1990年代以降已有学人试图梳理其诞生脉络的情况下,各样纷纭言说中,这一“常识”作为“知识”仍在四处流布,其真实性与可靠性依然未受到普遍质疑,且仍旧被赞扬或批评者作为重要的话语资源在使用。
“打孔家店”?“倒孔家店”?
含混不清的“打倒孔家店”一再进入知识系统的再生产这种现象,与人们强大的文化惰性有关,但也与既有研究成果未获重视及其所含缺陷有关。
在1979年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小型座谈会上,彭明指出,他和一些同志查阅《新青年》等报刊,以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易白沙等代表人物的论著,都未发现有“打倒孔家店”的记载。此后,韩达曾查阅“五四”时期包括《新青年》杂志在内的文献,并发表了论文《“打倒孔家店”与评孔思潮》(1982),编辑出版了《评孔纪年(1911-1949)》(1985),提请学界注意这一口号的虚无性;杜圣修在《关于“打倒孔家店”若干史实的辨正》(1989)中指出五四时代并不存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认为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者不是吴虞;严家炎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1989)中指出,当时并不真有“打倒孔子”或“打倒孔家店”一类口号,有的只是对孔子相当客观、相当历史主义的评价;宋仲福在《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考察》(1992)中主张不能给“打倒孔家店”以历史地位,因为它只不过是后来各种错误因素凑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冒牌货”,并建议在今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中,抛弃那困扰了人们几十年的“打倒孔家店”。
在考察“打倒孔家店”词组的缘起方面,韩达、宋仲福、杜圣修、严家炎、龚书铎等论者都追溯到了胡适所写《〈吴虞文录〉序》中的“打孔家店”。至于“打孔家店”怎么变成了“打倒孔家店”,则有衍生、错衍、衍导等说法。宋仲福在《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考察》(1992)中认为,“使用‘打倒孔家店’这种格式并使之固定化的人”是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和军阀。王东在《五四精神新论》(2009)中认为,胡适所言的“只手打孔家店”,在20 世纪 30、40 年代经人加工改造后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开始被曲解夸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
真实的拓展空间?
可见,论者们对这一口号的虚无性已有共识,对其与胡适、吴虞的关系也有了基本体认,但仍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首先,质疑其真实性的论者,屡屡提及他们翻阅《新青年》杂志及同期论著并未发现该“口号”这一经历,并由此否定这个说法的合理性。这显然欠缺对“五四时期”这个时限的警觉:《新青年》固然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刊物,但不是全部;陈独秀等人是五四时期的重要人物,但这些倡导“打孔家店”的老师辈,并不能代替后起加入“打孔家店”行列的学生辈。只有将考察范围扩大至《新青年》影响下各地蜂拥而起的报刊杂志,将考察对象扩展至“打孔家店”行列中的那些学生辈,系统考察他们的姿态、言辞的激烈程度、所“打”的内容上有无差异等,我们才能圆满回应“‘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时期的口号”一说是否真实的问题。
其次,在考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者与诞生历程方面,论者们已多关注到了胡适的《〈吴虞文录〉序》,但并未对其细加分析。比如,胡适为何要写这篇序言?他对吴虞的赞誉是否恰当?胡适所言的“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与后来人们反复截取的赞誉吴虞之词,在内蕴上吻合吗?此其一;其二,“打倒孔家店”一词到底是谁最先固定使用的?使用的背景是什么?言说的真实涵义又是什么?是否仅仅如一些论者所言的,是对胡适序言的“错衍”?其三,从胡适的序言到这种固定化使用之间,与“孔家店”有关的言说又经历了怎样的衍变?只有把这些纳入考量的范围之后,我们可能才会发现,这个话语的历史流变其实折射了其诞生前后整个社会的思想变迁史。
最后,在“孔家店”的内蕴方面,论者们多从各自的论述体系出发去加以阐释,而欠缺对这一话语随后的衍化历程的系统梳理。而弄清楚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者、《学衡》派、新生活运动提倡者、新启蒙主义者、新儒家、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期间的共产党人、台港学者与海外汉学家、198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对“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的不同理解、运用与阐释,也就明确了“孔家店”、“打倒孔家店”成为“口号”后的衍化历程,我们也许就理清了全盘反传统论、断裂论的历史由来,从而能更深刻、理性地回应这些论调本身。
因此,系统、深入地考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诞生与衍化问题,为“打倒孔家店”这一概念正名,或许是学界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的有效途径。这样沉潜下去所得的研究成果如果受到重视,或许就可以避免一些因话语的不可通约性而起的无谓纷争再度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