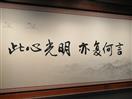认识和理解儿童是教育儿童的基本前提。如何认识和理解儿童?这在珍视儿童(童年)价值的今天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不论是家长、老师,还是其他相关的教育研究者,我们都深刻体会到认识和理解儿童的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困惑。本研究从现象学视域出发,通过对生活世界进行简要分析,以阐明儿童生活世界的含义;在此基础上,循着现象学的认识思路,试图探寻一条儿童生活世界的认识路径,为认识和理解儿童提供一种方法和途径。
一、生活世界简析及儿童生活世界的含义
要理解儿童生活世界的含义,首先需要阐明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晚年为消除近代欧洲科学危机提出的主题。在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史上,从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开始,自然科学就逐渐成为了纯粹研究事实的学问,目的在于追求可证明的、客观的知识。由此,带来了世界的二元分裂:自然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分离。由于自然世界对普遍性知识的追求,以往的直观自然逐渐演变为理念化自然,离人的意义越来越远。同时,又因为“其中的心灵的世界,由于它与自然关联的方式,当然并没有达到独立世界的地位”[1]的缘故,涉及心灵世界的学科,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对普遍性的追求之中。这带来了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泛滥,引发了近代欧洲科学的危机——人的存在与生命意义的缺失。针对这一危机,胡塞尔创立超越论的现象学(先验现象学),提出生活世界这一主题,以应对科学世界的危机。
在胡塞尔看来,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是一体并隶属于生活世界的。他指出,“客观理论在其逻辑意义上是植根于并奠基于生活世界之中,植根于并奠基于从属于生活世界的原初的自明性之中的。客观的科学作为前科学的人的成就,本身就属于生活世界的。”[2]而且,“我们的这些科学家毕竟是人,作为人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而生活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始终存在着的,总是预先给定的。因此,全部的科学就随同我们一起进入到这——纯粹‘主观的-相对的’——生活世界之中。”[3]可见,胡塞尔虽对世界作了“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划分,最终还是将“科学世界”纳入了“生活世界”之中。因此,有学者指出:“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经验实在的客观生活世界,一是作为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二者之间隔着一道先验还原的界限。”[4]
然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更多是观念形态的生活世界,其最终要还原到纯粹先验现象的生活世界(自明、超经验的世界)。恰如一些学者所言,“胡塞尔的现象学本身乃是一种旨在拯救现实人生危机的人生教育学,但过于依赖思想史和康德主义,使得他的人生教育学未能深入现实人生”[5]。胡塞尔的学生、另一位现象学大师(也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另辟蹊径,通过研究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些非理性体验,如“畏”、“怕”、“烦”、“孤独”、“迷失”等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状况及体验,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转向存在主义现象学,关注人的现实人生。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所有存在者中,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Dasein)这个术语来表示(人)这种存在者。……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6]因此,“彻底解答存在问题就等于说: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 [7]如此,关注现实人生就最终落到关注人这一特殊的存在者上——一切存在问题都是人的存在问题。要认识人的存在,就需回到人的现实人生中,去考察人这一存在者的历史演进过程。
循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主题及海德格尔的转向思路,在具体人生中,生活世界关注人(具体的人)的存在意义,是人在历史与现实场景中的完整展开。生活世界首先是当下科学态度中的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体现为人的当下状况及体验(这些状况及体验渗入了各种科学态度、意识观念);同时,又包含了人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意义生成的时空场域)。并且,人的当下状况及体验需要其发生境域的给予与说明。这意味着,发生境域赋予当下意义,具有奠基性、原初性。由此,笔者认为,儿童生活世界是儿童意义的完整展开:既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又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因此,认识儿童生活世界就要对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儿童如是”——进行描述;同时,还要追溯其发生境域,对“儿童为何如是”进行诠释。
基于此,笔者试图从儿童生活世界的认识原则、儿童生活世界的认识切入点、儿童生活世界的认识方法等方面入手,探寻一条儿童生活世界的认识路径。
二、儿童生活世界认识路径
(一)认识原则:面向儿童本身
现象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面向事物本身。胡塞尔认为:“合理地或科学地判断事物,这意味朝向事物本身(sich nach den Sachen selbst rich ten),也即从言谈和意见回到事物本身,追问它的自身给与(Selbs tgegebenhe it),并清除一切不合事理的先入之见。”[8]面向事物本身意味着,对于事物的各种态度,在没有明证它们是来自事物本身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它们采取“加括号”的处理方式,即把它们“悬置”起来,而从那些具有明见性的现象(本质直观、本原的被给予方式的显现物)出发,使得每一个判断和推论都有可靠的依据。可是,如何才能做到悬置呢?答案是:反思。“反思的基本态度在于,现象学家要摆脱这个由于存在信仰而被投入到课题对象之中的状态。他不是在直向生活的大河中顺流而下,而是要将自己升高到河流之上;他不再对意指的对象的存在发生兴趣,而是因此而成为‘不感兴趣的人’、‘不介入的观察者’。”[9]
从“面向事物本身”这一现象学原则出发,要认识儿童生活世界,就需要“我”(家长、教师、研究人员等认识主体)“面向儿童本身”。这要求“我”首先要回到儿童真实、生动、复杂的生活现实中,将儿童作为“我”的关注焦点,与儿童“面对面”。但是,当“我”面对儿童时,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对儿童的“先入之见”,即胡塞尔所说的“态度”:一方面,对儿童的认识,在“我”之外存在多种态度,这些态度会影响“我”对儿童生活世界的理解和判断;另一方面,在“我”身上,本身也存在许多关于儿童的固有的态度观念,这也会影响“我”对儿童生活世界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因此,为达到对儿童生活世界的合理把握,“面向儿童本身”意味着要“悬置”一切对儿童的“先入之见”。通过反思可以做到这一点。反思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我”对各种态度要“有意识”,即意识到影响“我”认识儿童的各种态度是什么;二是“我”对各种态度要“能意识”,即意识到各种态度是如何影响“我”认识儿童的;三是“我”对各种态度要“超意识”,即要能够从各种态度的影响中脱身而出,做各种态度的主人,而不是成为各种态度的奴隶。
因此,“面向儿童本身”意味着“我”要实现对各种认识“态度”的超越,以纯粹认识主体身份进入儿童生活世界,直面儿童。这是合理认识儿童生活世界的首要保证,也是认识儿童生活世界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认识切入点: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
“我”通过反思以“悬置”各种关于儿童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纯粹认识主体。那么,“我”凭借什么理解和把握儿童,即以什么为切入点认识儿童生活世界?我们可以对“儿童现象”进行分析,找到儿童生活世界的认识切入点。
“现象”(Phenomen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在德文中称为Erscheinung(“显现”的意思)。在胡塞尔的眼中,世界是现象的存在,现象意味着对象在认识主体的意识结构中的显现之物。“用简单的公式来表示:所有的分析都是对世界以何种方式显现给人们的解释性构造分析;现象学构造研究的基本课题是作为显现(Erscheinung)、作为现象的世界。”[10]与胡塞尔类似,海德格尔认为:“‘现象’一词的意义就可以确定为: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公开者。” [11]因此,现象学就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看它”[12]。
从以上对现象的阐释出发,“儿童现象”就是儿童自身显示自身者、公开者。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儿童自身显示自身者,即儿童自身“是其所是”的显现;二是儿童作为公开者,即儿童在“我”的意识结构中的“显现之物”。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依据,后者是前者在认识实践中的实现。因此,儿童生活世界的认识切入点就是儿童在生活世界中“是其所是”的显现。
回到具体的儿童生活世界,这种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是什么?在“我”的意识结构中的“显现之物”又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在实践层面上将二者澄清,才能对我们认识实践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否则,不仅不能对认识实践起积极指导作用,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认识混乱、不利于认识实践活动。循着这一思路,国外学者对“儿童视角”与“儿童的视角”的辨析对我们从认识实践上理解儿童现象有一定启发意义。
Kathy Sylva在《儿童视角与儿童的视角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区分了“儿童视角”(child perspective)与“儿童的视角”(children’s perspective):“儿童视角是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尝试‘由外及里’(outside in)地探究儿童所使用的方法,通常有社会学或语境心理学的考量;儿童的视角是来自儿童‘由里及外’(inside out)的观点或立场表达。换句话说,儿童的视角经常可以用儿童自己的话语、想法、图景来表达。具体来说,儿童视角是将成人的注意力引向对儿童感知、经验和行动的深层理解。因此,儿童视角是想要探寻并尽可能慎重、客观地还原儿童的视角的成人创造的。”[13] 通过以上儿童的视角与儿童视角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关系与现象学对“现象”的理解惊人的一致①:儿童的视角是儿童自身“由内及外”的表达,这类似于儿童“是其所是”的那个东西;儿童视角是成人“由外及里”地对儿童的视角的创造,这就相当于认识主体“如其所是”地反映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之物。笔者在比较的过程中,在“是其所是”的基础上加了“如其所是”(前面海德格尔在对现象的阐释中也隐约提到了这一点)。请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这就如同儿童的视角与儿童视角之间的区别一样:儿童的视角是儿童的本来面目,是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我们只有通过儿童视角,“如其所是”地无限接近它。换句话说,“儿童视角”表明了对“儿童的视角”的无限接近,这既是一种接近的无限可能性,同时又代表一种无限不可能性——二者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叠合。
理论意义上,就像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所揭示的认识过程一样,我们可以对儿童进行“是其所是”地理解和把握。但在实践层面上,我们一直都没有达到、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依据“儿童的视角”运用“儿童视角”,“如其所是”地理解和把握儿童。这一立场代表了对儿童的敬畏,也是不断激起我们对儿童生活世界进行无限探索的愿景与动力。在这种立场之下,一个最为具体的问题就是:在儿童生活世界中,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究竟是什么?回到以上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儿童的视角与儿童视角是两条相反的路径:前者是“由里及外”的表达,后者是“由外及里”的探寻。我们不能直接去探知儿童的“里”,但是,我们可以抓住儿童“外”的表达,去尽可能提高我们探索的儿童的“里”与儿童自身的“里”的吻合程度。儿童的“外”就是儿童在生活世界中的言行表达,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外在表达抵达儿童的内在深处。简单地说,以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作为认识切入点,就是抓住儿童在具体生活世界中的言行表达,通过这些言行表达,力图进入儿童生活世界。当然,外在言行仅仅是一把钥匙,打开门之后,我们能看见什么,能够解释清楚些什么,还得要看我们的方法运用。这就涉及到儿童生活世界认识路径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认识方法。
(三)认识方法:“聆听”儿童与回溯求证
当“我”投身到儿童生活世界之中,直面儿童本身,仿佛来到了黑格尔的“镜子”②面前:“我”正正衣冠,看看自己的装扮,深吸上一口气,拿起一把钥匙,打开了门,准备进入那个神秘的世界……
1.“聆听”儿童:把握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
如果说“我”在投身儿童生活世界、面向儿童本身时,找到了认识切入点——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那么,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找到了儿童生活世界的认识切入点,该怎样去把握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答案就是:“聆听”儿童!即在儿童“是其所是”的显现中,运用“我”作为认识主体的特性,去把握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
首先,“聆听”儿童意味着“无目的”地“听”儿童。这与胡塞尔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学概念——“明见性”——是相符合的。“胡塞尔将哲学中的本原被给予称为明见性(Evidenz)。明见性的特征是直观,在这种直观中,我以无兴趣的、不参与的考察方式看到对象,即看到某些普遍本质联系。只要事物是在此时此地的当下中显示给我,那么对这事物的感知便是直观。”[14]可以看出,明见性是事物“是其所是”的显现在认识主体意识结构中的反映,是认识主体对事物现象的最直观的把握。从明见性出发,在“聆听”儿童过程中,认识主体最初是处于一种“无目的”的状态:意识到目的、排除目的后而获得的一种状态。认识主体之所以要寻求这种状态,是为了实现对儿童“在此时此地的当下中”的显现(言行)的把握,获得对儿童的当下直观。这是认识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基础,也是认识整个儿童生活世界的基础。正如一些学者对明见性的解读:“哲学能断言的只应是在本原地给予的直观基础上对它来说可能的那些东西,不比这更多,也不比这更少。”[15]在认识儿童生活世界过程中,我们能够断言的,也只是在儿童当下直观的基础之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的那些东西。因此,通过“聆听”儿童把握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首先就是“无目的”地“听”儿童。
其次,“聆听”儿童意味着“有目的”地“听”儿童。在认识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过程中,认识主体“无目的”地“听”儿童,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认识的消极面——受制于儿童“此时此地的当下”。但是,借助于认识主体的“权能性”,“我”就能超越儿童本原的被给予方式的显现物,达到对儿童多种非本原方式的被给予之物的把握。关于权能性,“胡塞尔将这些在感知事物上出现的多种被给予方式称为‘映射’。这些映射中的一部分——当下进行着的映射——‘真实地’、直观地将事物显示给我,而其他的映射则是作为可能性而被我意识到的,我可以将这些可能性转变为真实的直观。这种可能性作为某种处于我权力范围之内的东西而被我拥有;因此胡塞尔将它们称之为‘权能性’(Vermöglichkeit)。……权能性的关系为我展示的可感知之物的游戏场被胡塞尔称为视域(Horizent)。”[16]正是借助于认识主体的权能性,“我”才能在把握儿童当下直观的基础上,将儿童非当下的一些内容纳入“我”的视域,“有目的”地“听”儿童,实现对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深层把握。也恰如胡塞尔所言:“对象所指的是比在任何被给予方式中显现之物‘更多’的东西。”[17]
第三,“聆听”儿童意味着对儿童当下的指向和构造。如果说明见性体现了认识主体消极的一面,权能性体现了认识主体积极的一面。那么,胡塞尔提到的“意向性”,则体现了认识主体能动的一面。胡塞尔认为:“意识是意向,即:指向对象。”[18]同时,“它(意向性)是指向一个意识自身的意义构造,在这种意义上,意向的指向就自然而然转化成一种意义的赋予和激活零散感觉素材的意向对象构造,意向性也就主要展现为一种构造性功能。”[19]正是认识主体意向性的指向和构造功能,将来自于儿童当下直观和非直观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
因此,“聆听”儿童表明,在认识实践中,只有建基于最能反映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直观材料,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深度结合,我们才能完整把握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进而向其发生境域迈进。
2.回溯求证:考察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
通过“聆听”儿童,我们实现了对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整体把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儿童为什么会有如此状况及体验?这就需要回到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中,去寻找答案。那么,如何才能回到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我们可以从胡塞尔提到的“时间”主题获得启示。
“胡塞尔的命题是:时间是——在奠基顺序的意义上——第一个被意识到的东西。意识是一条体验流,即一种流动的多样性……体验流的多样性的综合统一在胡塞尔看来就是时间性。”[20]这种体验流的多样性在时间顺序上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就此而言,儿童是由“儿童的过去”、“儿童的现在”和“儿童的将来”构成的完整统一体。并且,“通过回忆和期待,我将过去和未来当下化,即:我将现实的、当下的、或近或远的时间性‘环境’(Umgebung)当下化……所以,‘回忆’和‘期待’的被给予方式被归结到‘当下拥有’的被给予方式上。”[21]因此,不论是儿童的过去、还是儿童的将来,都将以“当下化”的方式凝集到儿童的现在之中。所有这一切,都以现在为坐标,一并融合于现在之中,即“本原的被给予的时间始终以作为其关系中心的现实当下来定位”[22]。这也是我们能够从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为突破口、对儿童生活世界进行研究的理由之一。
由上可以看出,“儿童的现在”是在“儿童的过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认识“儿童的现在”是为了“儿童的将来”或“将来的儿童”。我们要理解和把握儿童,就不能只关注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还必须回到儿童的过去,追溯其历史成因。因此,回溯求证是认识儿童生活世界、理解和把握儿童的必要环节。
要做到回溯求证,必须对儿童生活世界两条线索进行把握:一是横向的空间线索,二是纵向的时间线索。具体来讲,在空间线索上,就是要回到儿童生活的家庭、学校(幼儿园)、社区等场境中,面向家长、老师、同伴等相关人员,运用观察、访谈等方法,探究各种场境因素之间的联系及其对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影响;在时间线索上,主要通过访谈家庭成员、老师等,了解儿童的生活史(包括家族的历史状况、儿童的孕育过程及养育状况、儿童的早期经验、儿童的教育经历等),探寻儿童生活经历对其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影响。通过两条线索融织在一起,全面考察儿童在不同的生活空间中与世界互动的关系历史,揭示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演进过程。
正是通过回溯求证,我们进入了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发生境域,对儿童进行“为何如是”的诠释。这种诠释本身就透露了一种对教育的价值判断,引导我们体悟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生成过程,并对我们教育观念的革新、教育行为的改变提供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认识儿童生活世界又关照了“儿童的将来”或“将来的儿童”。如此,与胡塞尔的时间主题相联系,对“儿童如是”与“儿童为何如是”的探索,就将儿童的过去、儿童的现在和儿童的将来(将来的儿童)连在了一起,实现了对整个儿童生活世界的探索。
从现象学视域出发,儿童生活世界的含义及认识路径更多是一种关注儿童特殊的方法:在儿童生活世界之中,具体儿童及儿童的特殊需要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这不仅揭示了一条全面认识儿童、理解儿童的方法途径,还昭示了我们与儿童共同生活的教育伦理要求——基于儿童现实的、为了儿童的将来或将来的儿童作出教育观念的革新与教育行为的改变。
探寻儿童生活世界就是探寻儿童的意义,同时也是探求我们自我存在的意义。儿童生活世界是儿童成长的土壤,那是属于儿童的生长地基,具有最为本真、最为纯洁的意义。也是我们诗意的栖居之所。正如泰戈尔的希望:“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有一角清净地。”(泰戈尔,《孩子的世界》)然而,今天我们正在污染儿童世界的这份纯真。除非回到儿童的世界,找回纯真,如荷尔德林的诗句 “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荷尔德林,《人,诗意的栖居》)。否则,我们难觅返乡之途,终究只能做一个异乡之客。
注释:
①实际上,在《儿童视角与儿童的视角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著作中,著者也多次提到了“现象”或“现象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现象学这一思潮对西方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现象学理论本身对探讨“儿童视角”与“儿童的视角”的基础意义。见:D· Sommer,I· P· Samuelsson,K· Hundeide. Child Perspective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 2010.
②黑格尔曾用“镜面”对光的反映来比喻“反思”,循着黑格尔的这一用意,笔者主要借用“照镜子”这一过程来比喻认识主体通过反思悬置各种态度的过程。关于“反思”,黑格尔曾经有一段论述:“反映或反思这名词本来是用来讲光的,当光直线式地射出,碰在一个镜面上时,又从这镜面上反射回来,便叫做反映。在这个现象里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一个直接的存在,第二方面同一存在是作为一间接性的或设定起来的东西,当我们反映或(像大家通常说的)反思一个对象时,情形亦复如此,因此这里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不是它的直接性,而是它的间接反映过来的现象。”见:[德]黑格尔.小逻辑﹝M﹞. 贺麟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42.
[1] [2] [3][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7,157,158.
[4]朱刚.胡塞尔生活世界的两种含义——兼谈欧洲科学与人的危机及其克服〔J〕.江苏社会科学,2003(3).
[5]周勇.文学、电影与人生教育学——论教育学的现象学转向及其优化路径〔J〕.全球教育展望,2013(8).
[6] [7] [11] [12][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M〕.陈嘉映,王庆节 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4,9,34,41.
[8]张庆熊.“朝向事物本身”与“实事求是”——对现象学和唯物论的基本原则的反思[J].哲学研究,2008(10).
[9] [15] [17][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M〕.克劳斯·黑尔德 编,倪梁康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8,12-13,24.
[10] [14] [16] [18] [20] [21] [22][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克劳斯·黑尔德 编,倪梁康 张廷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8,10,6,18-19,20,20.
[13]D· Sommer,I· P· Samuelsson,K· Hundeide. Child Perspective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 2010:vi.
[19]高秉江.胡塞尔与西方主体主义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95.
The Meanings and Cognitional Path of Children’s Life-World under the Phenomenological Horizon
LI Xu1,2 LI Jing1
(1.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400715;
2.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550001)
Abstract: Based on the phenomenology horizon,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wo meanings of children’s life-world: children’s current status and experiences, namely " children being" and the realm of that, namely " why children being like that".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then analyses and demonstrates the cognitional path to children’s life-world which effectively describes "children being" and interprets "why children being like that": first, it is to take "facing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as a principle of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life world;second, to take" the appearances of what children being" as the entry point ;third, to take"listen to children"and"trace back and seek confirmation"as cognitional means.
Key words: phenomenology; life-world; children’s life-world; meaning;cognitional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