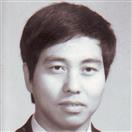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写下了古代最杰出的民族战歌《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是楚国举行国家祭祀典礼的完整乐章《九歌》中的一篇哀悼阵亡将士的祭诗。
诗人以雄劲的笔墨,在诗篇中描绘了激烈壮观的战争场面,歌颂了楚军将士为国捐躯的英雄业绩。首四句,在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中渲染了惨烈的战斗气氛和敌军阵容的强大,烘托了楚军将士勇猛的气概。接着诗人又概括而生动地描写了楚军身陷强敌的困境和义无反顾的顽强斗志。尽管全体将士在浴血奋战中壮烈牺牲了,但他们的壮举惊天地而泣鬼神。这六句是在更为炽热化的激战中,生动地刻画了楚军将士的忠烈形象。最后八句,诗人以慷慨激昂的语言赞颂了烈士们生作人杰,死为鬼雄的民族献身精神。
(包括《国殇》在内的《九歌》,是一组完整的祭祀乐歌,所祭的神祗,地位都很重要,诗中所描绘的祭祀场面,也颇为宏大。因此,这种祭祀活动,不可能是在地方上进行的,而只能是国家的祭祀典礼。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王逸认为《九歌》乃屈原被逐以后所作,这看来靠不住。写作这一组乐歌时,屈原理应还在朝廷供职。至于他是否已经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即所谓“遭谗被疏”则很难说。《国殇》所牵涉的战争背景,马其昶《楚辞微》认为是楚怀王时,秦楚丹阳、蓝田两战,楚军皆惨败而“兹祀国殇,且祝其魂魄为鬼雄,亦欲其助却秦军也。”这大体是可信的。)
诗人通过对失败战争的描写,表达了对楚军将士忠魂毅魄的庄严礼赞,深切地抒发了诗人热爱楚国的激情。但《国殇》虽是个人之作,同时也集中地表现了楚民族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可以称之为国殇精神。所谓国殇精神,概括地说,就是楚人的爱国尚武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楚地社会形态及楚地宗教观念有密切的关系,表现出个人与集体的高度融合。
一、楚民族的处境和尚武精神
《国殇》以残酷的格杀,惨重的牺牲,塑造了楚军将士奋勇杀敌的英雄形象,体现了楚人的尚武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这种爱国尚武精神是楚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斗争中形成的。
楚发迹于商周之际,约在商代中期才辗转迁徙到荆山之地,如《诗经·商颂·殷武》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史记·楚世家》载:“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昆吾和彭祖是季连的大兄和三兄。《史记•楚世家》又载:“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还载:“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楚族很可能由于季连后代也卷入了中原地区激烈斗争的漩涡,而被迫南迁的。楚居荆地后,长期受到了中原地区的歧视和征伐。商王朝曾对楚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战。《竹书纪年》记:“商成汤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及荆,荆降。”《诗经•商颂•殷武》云:“挞被殷武,奋伐荆楚,穼入其阻,裒荆之旅。”这是商代武丁时对楚的远征,为的是楚人对殷人“不来享”和“不来王”。西周时,楚先祖“鬻熊子事文王”,(《史记•楚世家》)故其曾孙熊绎始封子爵,有楚国,这是楚首次获中原天子封号,确立了属国关系。但周室也是对楚持岐视态度。《国语·晋语》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周天子根本不承认楚的诸侯地位,不仅取消了楚子结盟资格,还只给予“守燎”之贱职,视楚如同鲜卑之流,这是对楚难以容忍的凌辱。周楚矛盾趋向激化。周成王晚年就不惜劳师,亲率大军南征楚了。楚虽南居僻隅,但周视楚为异类和心腹之患,常兴师征战。(周昭王三次伐楚,周穆王三十五年和周共和行政二年两次伐楚。周宣王五年,方叔率周师又伐楚。《诗经·小雅·采芑》就是颂扬周军这次伐楚的武功的,其中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这咬牙切齿的训斥,显示了周对楚人桀骜不驯的敌视,周室伐楚是为达到“蛮荆来威”之目的。)
楚人在被压抑、被欺侮、被损害的逆境中并没屈服。《竹书纪年》载周昭王三次伐楚皆无成功。第一次遇大兕而还,第三次昭王死而退,可能是遇到了楚的抵抗,第二次周军“丧六师”当为楚人武装击败,至于“天大曀”乃是史官托辞饰语,不足为信。楚人在历史的教训中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楚国是无以生存和发展的,是无以改变其屈辱地位的。《文献通考》曰:“(楚)武王始为军政。”楚自武王之世,对外征战不绝于史,表明了楚人正式制定了以武立国的方针。熊通三十一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左传·桓公二年》)楚国的武力已构成了对中原诸夏的威慑。(熊通在三十五年伐随时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过二年,他便公然自称武王。楚武王以雄厚的军事实力登上了春秋国际舞台。《左传·宣公二年》云:“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庄王堂而皇之观兵问鼎于周,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周王室屈尊派王孙“劳楚子”与往昔熊绎“守燎”相比,显然是沧桑之变,说明了楚的强大和周室的衰微。历来受到周人压抑的楚人,以尚武精神洗涮了历史的屈辱。这对楚民族来说,怎能不对前途充满信心呢?)
但中原之人并没因楚的强大而放弃对楚的歧视。中原人历来称楚为“蛮”。《公羊传·僖公四年》曰:“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商周兴兵伐楚就是把楚当作野蛮民族而试图征服的。楚人遭到的民族歧视在心灵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重荷,激励了他们自强不息的斗志和改变现状的愿望。(鲁国季文子说:“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左传·成公四年》)宋公子目夷说:“楚,夷国也,强而无义。”(《公羊传注疏》)中原视楚为异族的偏见,已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压抑力越大,发泄力越强。《国殇》中楚军将士寡不敌众仍争先杀敌的尚武精神显示了这种力量的强大。
楚国对来自蛮夷之地的侵扰也进行了长期、曲折的斗争。楚在与中原的对抗中,始终谨慎地注意对待周围各族人,想在南方取得盟主地位,以利发展自己。《史记•楚世家》言:“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即反映了和睦政策的成功。但欲称雄南方毕竟还需以武。《史记•楚世家》载文王时:“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另外,楚周围的小国和蛮夷之人政治目光短浅,易被人利用,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背叛楚国,楚有时不得不诉诸武力。《左传·文公十六年》记:“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据说这是南蛮对楚一次规模最大,情况最复杂的挑衅,经过这次战争,楚灭庸,征服了大江以北的南蛮。蛮夷之族的经常侵扰迫使楚更为急切需要增强武力。(楚成王使人献周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势失如诸侯的周王朝欲借重楚国之武力镇抚蛮夷,以屏障中原。楚人在与蛮夷的反复斗争中也表现了尚武精神。)
来自中原和蛮夷的武力威胁和民族歧视,客观上促使楚人形成了爱国尚武精神。《国殇》虽然描写的是一场楚国失败的战争,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失败的楚人,这正是楚人在与中原和蛮夷的不断征战中养成的勇武、刚强、慓悍的民族性格的袒露,这种性格所迸发出的爱国主义尚武精神,使楚民族更为自尊、更为自强和更为自信。楚人先后吞并了六、七十个国家和部族,由“辟在荆山”的子男之邦发展成为“地方五千里”的军事强国,昭示了楚人武功之威。尽管后来楚主要因政治上的失策和外交上的失利为秦所灭,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最后灭秦的还是楚人,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奋起响应的项羽、刘邦皆为楚人。这不是历史的巧合,也不是历史的循环,而是深蕴于楚人之中、《国殇》中所表现的尚武精神的继续发扬。
二、楚地社会形态与国殇精神的关系
楚地社会形态比较落后,比北方晚进入农业社会。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史记•楚世家》)因此,楚人正式开发荆山之地为时很晚。《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令尹子革言:“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辟在荆山”、“以处草莽”及“跋涉山林”勾勒了楚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恶劣;“筚路”、“桃弧”及“棘矢”则表现了楚人征服自然的生产水平低下。《左传·宣公十二年》又载晋栾武子语:“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说:“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说明楚人自西周以来直至春秋初年,始终生活于狭小的南方荆地的荒山野林之中,以简陋的生产工具,艰难地聊以谋生。《剑桥古代史》认为:“农业的发生和农村的出现,不论在新世界还是旧世界,在东亚还是西亚,在东北非还是东南欧,最早都在山地或高地,而不在河流平原或三角地带。”此时中原地区农业已相当发达,而楚人还没走向平原大川,仍在荆地垦殖山林。由于山地不便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故楚地虽有农业生产但很不发达,而狩猎经济则是其主要谋生手段。《吴越春秋·勾践外传》记载楚人陈音语:“(楚地)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随着楚国的武力扩张,楚疆在楚平王时已达“土数圻”。(《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威王时竟达“地方五千里”。(《战国策·楚策》)《淮南子·兵略训》云:“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楚地已有半天下了。《墨子·公输》曰:“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楚地已是何等富庶。《汉书·地理志》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可见楚地自然资源丰富,百业俱兴,劳动多样化,而不象北方那样人多地少,因此不必精耕细作,其农业占经济的比重不如北方。
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社会形态的交替乃是一种渐变,不可能有明显的界限。楚始立国时农业不发达,狩猎占经济比重较大,故社会剩余产品较少,阻碍了楚人进入阶级社会的速度,后楚地渐大,但地广人少,自然物产丰饶,使贫富分化不如北方那么剧烈。因此楚整个社会较长期地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上,在整个华夏由氏族社会向宗法制社会转变时,楚国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氏族社会的传统。
氏族社会相对来说,等级制度不很严格,部落首领与民众更为接近。周成王虽封熊绎为子爵,但他仍“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过着艰苦的生活,还没成为凌驾于公众之上的特殊人物,说明了楚并不象周那样等级森严。《左传·庄公十九年》载:“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楚王首战败于巴人,大阍鬻拳拒其于门外,激其再伐黄,以挽回前败。鬻拳不以位卑而迁就楚子败绩,楚王不以位尊而谴责鬻拳弗纳,而是复出伐黄以致病死。这种无视尊卑的君臣关系在中原是难以想象的。《国语·楚语》记楚昭王时,吴人攻入楚,昭王出奔,蓝尹亹拒绝载其渡成臼之水,说:“自先王莫坠其国,当君之世而亡之,君之过也。”臣下置君王危难而不顾,反而指责君王败弃国都,如在中原将难免遭杀身之祸,但后来经子西调停,楚王并无以权势压人,而是君臣两相安。故宗法制的君君臣臣之说在楚国并不特别讲究。正是这种不受宗法制等级划分严重束缚的社会,楚人才会有更大的热情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才会更加自觉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他感到自身的利益与氏族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当自己的民族、国家与外部发生战争时,楚人便会毫不犹豫,自觉而勇敢地为民族、为祖国而战。《国殇》中那些将士坚毅勇武地为国赴难,甘洒热血于疆场的自觉行为体现了热爱祖国的集体精神。《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楚康王使人谓令尹子庚言:“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这种对君王施加“死不从礼”的压力,表现了楚人普遍关注国家战事的热情,是一种集体精神的力量。(鲁庄公四年,楚武王将伐随,临行时夫人邓曼说:“余心荡。”但邓夫人非但没有劝阻武王出征,反而说:“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左传·庄公四年》)后武王出征,死于途中樠树之下。邓夫人视丈夫生命为小事,而把军队出征作为大事,这与北方宗法制视君王为至高无上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从邓曼身上可窥见到楚地集体精神所赖以产生的广泛社会基础。)
《国殇》与《诗经·周颂·武》同为国家祀典的祭歌,但却表现了保留氏族社会传统的国家和宗法制国家的不同精神面貌。《国殇》颂扬的是楚军将士的献身精神,强调的是群象,氏族社会色彩强烈;《武》歌颂的是周祖先的文德武功,强调的是偶象,宗法社会的等级思想浓厚。从这两篇诗歌的比较中,可更为清楚地看到楚军将士的英雄群象,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楚民族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宗法制社会不可能有的,而保留氏族社会传统的楚国特有的产物。
三、楚地宗教意识与国殇精神的关系
先秦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南北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即恪守“礼”的北方史官文化和浓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许多传统的南楚巫官文化。楚地巫官文化具有强烈的宗教神话色彩,使楚人精神生活散发出浓重的神秘气息。
宗教是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相联系的。原始宗教用鬼神解释世界一切,是人类早期认识世界的方法。生活于先秦时代的人,完全不信鬼神的,恐怕不会有的,但对鬼神的态度,往往是因族而异、因人而异。孔子说:“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篇》)楚人则是事鬼敬神而近之。《论语·述而篇》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说孔子是不讲鬼神的;而屈原则是“陈事神之歌”的。周《武》与楚《国殇》皆属庙堂之音,但后者显然比前者宗教色彩更浓,鬼神气息更重。《武》是模仿周武王伐纣的武舞,其中有举袂、顿足、持干戚作击刺之状。孔子认为这种炫耀武功的乐舞,不利于以德教化人,是“尽美矣,未尽其善也。”(《论语·八佾篇》)《国殇》描绘了楚人“操吴戈”、“被犀甲”、“带长剑”、“挟秦弓”浴血鏖战的场面,表达了屈原的爱国激情和审美意识。孔子提倡施仁政,崇尚理性,注重教化,故认为描写战争景象的作品不是尽善的,表明了他对暴力的否定。屈原受到楚地宗教神话的熏陶,具有丰富的想象和热烈的情感;他热爱祖国,以“为美政”(《离骚》)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主张对内举贤授能,变法革新,对外联齐抗秦,从而使楚国兵强国富,达到一统天下之目的;他亲手创作了《国殇》这篇表现战争景象的楚地庙堂祭歌,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体现了楚人的精神面貌。因此,屈子并不一概否定暴力,而是积极主张以武力保家卫园,统一天下。《国殇》在作者自己看来,不仅应是尽美的,还当是尽善的。从屈子和孔子两位南北文化巨人的不同态度,可见南北两种文化的各自特色了。楚地因有浓厚的氏族社会色彩,故宗教也保留了人神相杂,灵魂永存等原始宗教的一般特点。王逸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这说明了楚地盛行原始的巫术礼仪风习。楚人以祭祀和卜筮作为与鬼神交通的手段。卜筮常用于消除疑难,预测前途,而祭祀则是祈求鬼神保佑。《楚辞》的许多作品反映了楚地的宗教活动及其特点。《九歌》是一组祭祀鬼神的诗歌。其中《东皇太一》是祭祀上帝的,《东君》祭祀的是太阳神,这两篇诗歌中都有巫的活动。(巫是与神打交道的人,男女皆有。巫与神的交往表现了楚地人神相杂的宗教特点。其中《云中君》写巫女等候云神的降临,以候人之难,相思之苦,抒发了人神恋爱的情调。)《大司命》是写巫女迎接大司命,表现了巫女对大司命的怀恋之情和失恋之意,也有人神相爱的意味。人死为鬼,楚人对鬼非常敬重,奉祀唯谨。鬼其实也是神。《国殇》就是祭祀为国阵亡将士的鬼魂,表现了肉体虽亡,精神不灭的宗教观念。(楚人还有招魂的习俗,《招魂》、《大招》就是楚地招魂的诗篇。这两篇诗歌的作者是谁,所招谁魂,尚有歧说,这且不谈。从这两篇诗歌的内容来看,《招魂》是自招生魂。据考,两湖、江西一带,在解放前,民间还残存活人自招其魂的风俗。《大招》是为死者招魂。这种魂不论生死皆可招的宗教活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楚地人鬼相通,生死互混的宗教意识。)
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宗教并不完全是盲目的行为,一定的宗教、巫术都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氏族部落间、民族间在经常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需要每个人对部落、民族的命运承担责任,需要每个人对部落、民族的存亡作出牺牲,这时,宗教便会有意无意地被用来充当加强部落或民族凝聚力的工具。楚民族的战歌《国殇》产生的凝聚力就表现了宗教的这种功能。《国殇》把崇高的为国献身的精神引入到宗教的神秘仪式中来,为感召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楚人共同抵抗民族的敌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人事鬼敬神表现在《国殇》里,就是尊重战死者,歌颂战死者。“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这两句是诗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对烈士们报国之躯虽亡,爱国之心犹存的赞美,丝毫没有颓唐之伤感。原始宗教认为,生命是不会消亡的,死只是生命形态的一种转换,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鬼神世界与人的世界没有明显的界限。这种观念在《国殇》中得到了显现。“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这两句写全体阵亡将士肉体虽亡,但他们的英魂已化为鬼雄。诗人表达了楚民族生命永存、灵魂不死的宗教观念。这种观念在楚地对调动人们自觉消除对死的恐惧,唤起人们敢于为国牺牲的激情具有很大作用。《说苑·立节》载:“楚人将与吴人战,楚兵寡而吴兵众。楚将军子囊曰:‘我击此,国必败,辱君亏地,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国郊。使人复于君曰:‘臣请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为利也,而今诚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楚国终为天下弱矣。臣请死!’退而伏剑。”子囊处在要么辱君亏地,要么临阵遁逃的两难境地。他从民族利益出发,选择了黜兵之路,但怕后世效尤遁者无罪,致使楚国势弱,便毅然引咎自决。(楚武王时,莫敖屈瑕伐罗失败,自缢于荒谷。晋楚城濮之战,楚师败绩,楚主帅子玉不待复君命即自杀了,副帅子西也要引咎自缢,因上吊绳断,楚王使者到,才止其死。晋楚鄢陵之战,楚军败北,尽管楚共王亲自承担责任,统帅子反仍自杀谢罪。)楚军将帅以死谢罪,确是对战事的极端负责和具有尚武观念,但也有对死不存在很大恐惧的宗教因素。文明程度越高,理性越强,人神关系越分隔,对生死概念越分明,往往就越增加对死的恐惧感。楚地宗教具有人神相杂,灵魂永存的特点,对楚人消除人所必然有的惧死感,发扬勇于为民族献身的英雄主义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可见,巫官文化和原始宗教被楚人用来激发民族精神与马林诺夫斯基所述的宗教性质是一致的。
四、个人与集体高度融合的英雄主义
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纷起,尚武成为普遍现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皆以武力争霸称雄。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说:“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墨子·兼爱》)这话道出了当时诸侯间战争频繁的事实。
因社会形态不同,地区不同与文化不同,尚武表现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秦人也以好武著称。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恐怕与秦人的好战有关。秦国僻处西方,文化落于诸侯国之后。文公二十年,秦采用西戎野蛮法律,始有灭三族之酷法。秦先祖“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史记·秦本纪》)秦又受周室之命,屡屡征战西戎以保周朝之祚,因有功,周平王始封秦襄公为诸侯之爵。秦是在与西戎的战斗中逐渐强大起来的。秦虽发展成为西方大国,但因其采用落后的制度和文化,而仍被华夏诸侯视为戎狄之邦,秦国受到的这种歧视与楚有相似之处。但秦历来与商周关系较好,并不曾遭受到象楚那样被频频征伐的厄运。孝公在位时,秦国实行商鞅变法,立等级,行法治,建立了专制主义的地主政权。此后,秦的政治纳入了法家学说铺设的政治轨道。秦国君主专权,刑罚残酷。这种政治对富国强兵,统一中国曾起到巨大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黑暗一面,曾使秦强大的法治成了亡秦的政治。商鞅变法确立了奖励军功的制度:立军功者,各按功劳大小受爵赏;私斗者,各按犯罪轻重受刑罚。几年后,秦国“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这种以功授爵的军事制度,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秦人参战的热情,促进了统一中国的成功。但处在严厉的专制社会等级制度下的秦人,与处在保留氏族社会传统的国家中的楚人相比,更为缺少人身的自由,他们参加战争,主要是为了代表国家利益的地主统治阶级,至于受功得赏,只有视战争的结果和自己在战争中的表现而定,不可能人人皆有功赏。因此,秦人参战,更多的是法律的强制要求。秦国实行连坐、灭族的酷刑就是对个人自由的摧残。楚国的法律传统比较重视个性。如若敖家族谋反被庄王攻击,这个家族成员斗克黄正出使齐国,回归,途径宋国听到变故,有人劝其不要回楚国,但他认为不能弃君命,仍回国复命并自囚请罪,而庄王却仍让他官居原职。再如斗克黄的后人斗成然,因骄纵为平王所杀,但平王仍以其子斗辛为郧公。这种一人有罪而不诛连家族的楚法,说明了楚国对个人较为尊重。秦国则把个体牢牢拴在国体上,不允许有个体的自由。因而,在秦严厉的军事制度下,秦士兵往往被当作奴隶来驱使,士兵身份相当于奴隶。秦始皇兵马俑的秦军阵容如此强大,但却看不到活生生的个人,个体被集体湮没了。因此,秦国尚武特点,主要表现为有严格的军事制度,缺乏象楚人那样的个人精神。
向来又有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的说法。所谓慷慨悲壮者,即城市发达地区的游侠之士。可能因刺秦王的荆轲活动于燕赵之地,而有此说。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这是对游侠比较中肯的评价。荆轲是游侠中的突出代表人物,先祖为齐人,生于卫国,因不为卫所用而游侠于燕赵。他好读书击剑,能歌善饮,喜结豪贤长者。燕太子丹曾于秦做人质,秦王待之不善而结怨。太子丹逃归国后,常思报秦之仇,因燕国武力不足以敌秦国,而只得以行刺秦王来报家仇雪国恨。太子养荆轲于门下,以厚礼待之,授其刺秦王之任。临行,太子与客宾送荆轲于易水之滨,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声悲壮凄凉,表现了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荆轲刺秦王虽未遂,但那种孤身闯虎穴,勇为他人献身的精神得到了千古流传。这只是一种个体精神的尚武行为,对《国殇》中那充满集体精神的楚军将士的群体来说,显得力量太单薄,形象太渺小了。燕赵慷慨悲壮之士式的体现个人精神的英雄行为,与楚人充满集体精神的英雄行为相比,所起作用颇为不同。秦一统天下后,六国多复仇之事。如燕人高渐离继荆轲之志,置铅于筑中,击秦始皇不中而被杀。韩国公子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史记·留侯世家》)得力士,以铁椎于博浪沙击秦始皇,未遂而逃亡。这些以个体力量消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个体对像的英雄行为,虽使秦王朝大为震惊,但终究不能消灭秦王朝。而楚人则是以集体的力量燃起了反秦农民起义的烈焰:陈胜、吴广于大泽乡以“大楚兴,陈胜王”(《史记·陈涉世家》)的狐鸣之声,聚众反秦;项羽举吴中八千精兵,刘邦收沛子第二、三千人相继反秦。楚人高举“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的旗号,汇合了天下反秦力量,终于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楚人的集体精神在灭秦的战斗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楚国有着与中原、蛮夷长期斗争的历史。楚人遭受民族压迫很深,楚国又长期处在具有氏族社会传统的阶段,阶级压迫较轻,因此,楚人更为尊重个性,个人的生存也更依赖于整个氏族社会。《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有鄢陵之败,终生自愧,常以为训,弥留之际还要求大夫们在其死后加上“灵”或“厉”的恶谥,以负败绩之责。楚共王并不以为联即国家,而是置身于整个民族之中,不仅重视自己的职责,还把自己的职责与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个人精神与集体精神的一致。《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吴师攻入郢,昭王出奔,楚人“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率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楚人在没有将帅指挥时,仍能自发抗击外侵之敌并取得胜利。这是自觉的个体精神与民族的集体精神所表现的英雄壮举。《淮南子·修务训》载:“吴与楚战,莫嚣(钱别驾曰:“莫嚣即莫敖。”)大心抚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强敌,犯白刃,蒙矢石,战而身死,卒胜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几乎。’遂入不返,决腹断头,不旋踵运轨而死。”大心的形象多么像《国殇》群象中的一员!《国殇》中“矢交坠兮士争先”的群体英雄形象,正是由无数的大心那样的形象所构成。表现了个人与集体高度融合的英雄主义。氏族社会中的个体相对宗法等级社会中的个体来说,具有更多的个性尊严,当与民族的敌人作战时,更易激发为民族而战的自觉性,战斗中,也会表现得更为刚强、坚毅和勇敢。因为,这种独立而自由的个体意识到他为之负责的是整个民族的利益,自己与整个民族是不可分的,自己的生命与整个民族是共存共亡的。屈原在《国殇》中描写的楚军将士义无反顾,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正是个体精神与集体精神的结晶,表现了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
楚民族的国殇精神,乃是人类早期社会中的英雄主义。楚人这种英雄主义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与等级社会中的爱国主义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爱国主义是集体利益的表现。等级制越发展,普通民众从国家中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少,那么,其爱国热情也就越低。因此,我们不能要求奴隶社会的奴隶爱奴隶制国家,也不能要求封建社会的农民爱封建制国家。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皆是封建士大夫的爱国之举。这种爱国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维护封建地主利益的,当然也有抵御外侮的一面。等级社会中,普通民众抵抗外侵从根本上来说,是为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楚人处在没有严格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具有氏族社会传统的集体利益,能较好地体现普通民众的个体利益,而个体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集体利益的保障。故楚人的爱国主义较好地体现了集体利益,不像等级制社会所谓的爱国主义只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
现在,既不能恢复氏族社会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不可能恢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所谓爱国主义。但在今天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的爱国事业中,屈原《国殇》中那种爱国主义精神将仍能起鼓舞作用,并且将会激发出亘古未有的,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载于《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3期46-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