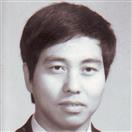1.引语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通过对中国农村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斗争的描述,展现了中华民族生活的历史面貌,从而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吴炫说:“中国作家的文化寻根文学和新潮文学在1985年前后同时产生,而且在‘寻找’上是殊途同归的——中国作家已经被‘寻找的惯性’所驱使而不自觉,只不过前者是从传统文化和被文化所遮没的原始土壤中去寻找价值依托,后者则是从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中去寻找价值依托。”[1]新时期的寻根文学和新潮文学在文坛的辉煌期都很短暂。尤其,寻根文学因被形式所累,在内容上陷入了迷惘的泥潭。但寻根文学毕竟开掘了探讨传统文化的先河,对激活新时期文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寻找的惯性依然存在,寻找的热情并未消退。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作家钟情的主要是中国非主流的、非规范的文化,那么90年代初,陈忠实的《白鹿原》则对历来奉为是中国主流的、规范的传统文化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白鹿原》是寻找惯性的产物,但其意义不仅对寻根文学带有终结性的清理,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么,这部新时期现实主义作品到底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呢?
2.构筑传统宗法社会
《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了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深谙巴尔扎克的创作之道,在写这部作品之前,阅读了中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研究了中国近代史和某些文化史方面的专著,查阅了地方志,在此基础上,又调动自身积累,精心为读者构筑了一个传统宗法社会。
“五四”以来,推翻传统宗法社会,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是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但现代史上传统宗法社会并没因此瓦解,而是与现代政治社会同存并在;儒家文化仍作为传统主流文化影响着社会生活。土地革命的完成使传统宗法社会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但儒家伦理道德却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灵魂深处。革命之后的任务是重建,历史证明,成功的重建往往只能是通过改造传统的创新,全盘否定传统无疑难以重建,甚至还会引起社会混乱。因此,《白鹿原》用写实手法构筑的传统宗法社会,对重新认识传统宗法社会、勘探传统主流文化,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反省新时期文学创作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旧中国是以小生产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上自最高封建统治者下至乡村基层中的宗法组织的族长,构成了有序的宝塔形的封建等级统治框架。传统宗法社会是靠儒家文化而“千秋万代”的。宗法社会的内部矛盾,如小说展现的白、鹿两家的斗争总是局限在这有序的宝塔形的封建等级统治框架中消长变化。因此,白鹿原的宗法社会组织在动荡的政治变革发展中显示出特有的稳定性。白嘉轩的族长地位比鹿子霖的乡约、保长要牢固得多;族长更多体现的是文化性,而乡约、保长更多体现的是政治性;新中国成立后,鹿子霖因乡约、保长的身份与经历,立即受到新政权的打击,而白嘉轩的族长身份与经历,由于远离政治而未受到清算。
宗法社会制度以血缘为基础,较少受到法律的制约,而是以道德伦理的原则进行自我约束,往往不与政权发生关系,而是从内部利益出发进行自我管理。在白鹿原,朱先生精心制定的乡约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族规,鹿三刺死淫荡的儿媳小娥,被视为维护道德伦理的义举。宗法社会的乡约族规融权力、法律、道德和伦理为一体来整合内部的人际关系,某种程度上比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更为严密更为细致。历来,政治观念的改变比宗法观念的改变要容易得多。因为,政治观念的改变往往可以借助于外在的强制手段来实现,而宗法观念的改变总是难以依靠制度约束来奏效。《白鹿原》再次提醒了我们。
小说的中心人物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理念的化身。他一方面谨奉儒学操守,一方面坚持农业劳动;既尊奉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原则,又耍狡诈、施阴谋来攫取别人的风水宝地。他的儒学人格在小说中凸现出世俗的多面性、复杂性,这使得他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文学形象。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白嘉轩身上,较完整地体现了儒家文化“仁”的特征。他是地主,雇有长工,但与长工鹿三之间毫无冷酷的阶级对立关系,两人亲如兄弟,还让女儿认鹿三为干爹。鹿三的儿子黑娃,当了土匪,用棍子打折了他的腰,落下了终身残疾,但当黑娃被判死罪,他却以德报怨,还想方设法救黑娃。他与鹿子霖为争夺白鹿原的家族统治虽争斗激烈,而鹿子霖吓疯后,他想巧取鹿子霖慢坡地时,却抒发了由衷的忏悔,面对鹿子霖的疯言疯行,还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白嘉轩身上充分表现了“仁者爱人”的儒雅姿态,这是儒家文化熏陶而成的,可以说是一种率真而自然的流露。如果说这也是虚伪,那么,应该是白嘉轩真诚地奉行了虚伪的儒家文化。“仁”是调整宗法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总纲。但“仁”模糊了阶级关系,妨碍了革命斗争,对社会变革具有排斥作用。白嘉轩最后无法理解儿女的人生道路,不能融入发展的现实社会,不能说与他恪守“仁”无关。
“礼”是儒家文化要求宗法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尊卑长幼有序”的道德伦理秩序。如果说“仁”是白嘉轩修身养心的自律的基本原则,那么“礼”则是他治理家庭、管理宗族的主要准则。身为家长的他,当得知心爱的女儿白灵私自离家参加革命时,断然宣布不认这个女儿,有人问起白灵,他则说“死了”。男儿尚且应“父母在,不远游”,何况女孩?白灵的出走成了恪守道德伦理的白嘉轩觉得难忍的心病。身为族长的他,无论在处理长子白孝文和小娥的奸情,还是惩罚小娥和狗蛋所谓奸淫罪,都无亲无疏,铁面无私,忠实地维护了封建礼法秩序。儒家文化的“仁”与“礼”是相辅相成的,讲“仁”须遵“礼”,否则就是无君无父无尊无长。“礼”是维系宗法社会伦理等级的准则。“仁”与“礼”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宗法社会正常运作方式的依据。
作者在完成白嘉轩儒学人格过程中,以各色人物为烘托,所有的人物的命运的变化无常都反衬出他那有惊无险命运的持重沉稳。白嘉轩的命运体现了中国农村宗法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结构形式和运作方式。
陈忠实通过《白鹿原》,为我们构筑了传统宗法社会的面貌,写出了巴尔扎克所说的“民族的秘史”。在新时期文学中用当代人的手笔把中国农村宗法社会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来观照,陈忠实当属第一人。黄子平说:“罗兰·巴特将长篇小说看作资产阶级整理经验世界以构成有序体系的工具”。[2]这部小说在“整理经验世界以构成有序体系”方面有一定价值,为当代读者了解传统宗法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文本。
但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著作,文学世界不是现实世界。陈思和指出:“万里长城和霍去病墓石刻,历史学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它在时间上的价值,政治社会学家可能关心的是论证奴隶的智慧与血泪,而对一个文学家来说,他惊叹的是长城之雄、石刻之奇,并从雄与奇的美学特征中感悟到中国文化的审美价值。”[3]《史记》之所以成为不朽的文学作品,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历史真实,而恰恰是由于其中凝聚了司马迁对历史真实的个性化理解,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价值。无论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无法摆脱自我理解来描述历史的真实。司马迁笔下的历史真实是经过司马迁筛选、整合过了的历史真实;同样,陈忠实笔下的传统宗法社会也是经过陈忠实筛选、整合过了的传统宗法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为主的儒道释价值循环互补体系,这种自足的互补体系,制约了文学创作。司马迁在“黄老”之学盛行的西汉初期,能不拘于当时的显学,肯定了儒学中他认为合理的成分,体现了个性化理解,提供了独特的审美价值。《白鹿原》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凝聚了作家对传统宗法社会的了解,但是由于缺乏作者个性化的理解,便无法提供独特的审美价值。陈忠实笔下的传统宗法社会在展现复杂的社会矛盾时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使作家无法构筑独特的传统宗法社会。小说中白、鹿两家的矛盾在道德、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展开显示得不够充分,致使对传统宗法社会的特征及内在矛盾的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所以作家对传统宗法社会的认识难免肤浅。如果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对封建世袭家族的描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必然衰败的迹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对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描述,展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征兆,那么陈忠实的《白鹿原》对传统宗法社会的描述,揭示的是什么呢?我们似乎没有看到导致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内在矛盾的依据。“秘史”的神秘感有余而独特感不足。由于作家对传统宗法社会缺乏个性化的理解,没有为我们提供如何突破传统文化的任何新的启示,从而也无法完成对政治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穿越,大大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
吴炫认为:“‘形象——个像——独像’就体现为文学性增强的过程,也是对作家要求越来越高的过程。”[4]白嘉轩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在新时期文学中虽有突出表现,但放在文学史里看,并无独特的表现,远没有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鹿鼎记》中的韦小宝那样,成为“独像”。贾宝玉、韦小宝作为叛逆形象对都是传统文化中的另类,构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像”,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提供审美价值,只是对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但文学的根本任务则是:不断提供独特的审美价值。曹雪芹笔下的具有独特处世原则的贾宝玉是为人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是塑造吝啬鬼,巴尔扎克笔下的欧也尼·葛朗台和吴敬梓笔下的严监生由于两人行为方式不同,也各自为人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价值。白嘉轩只是无数儒家文化卫道者中的“个像”,他的处世原则、行为方式,我们都似曾相识,不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
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固然不是历史教科书,但作为“民族的秘史”的文本应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穿越历史,对既定的历史有独到的、个性的理解。因此,《白鹿原》与《红楼梦》相比,既缺乏对客观世界的深刻把握,又缺少主观认识的独特理解。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白鹿原》无法穿越现实世界而达到文学世界的创造境界,终于没有修成文学创新的正果。
3.颠覆经典阶级斗争
新时期文学能联系近现代革命斗争史,比较成功地大规模描写阶级斗争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就目前而言,当数《白鹿原》。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逐渐形成了将阶级斗争作为母题的革命文艺,经典阶级斗争创作模式日益发展成形,到“文革”,最终完成了对阶级斗争描绘的彻底经典化。
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并非阶级矛盾都导致斗争,而且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仅仅是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只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但是,文学作品中的经典阶级斗争创作模式,不仅将阶级斗争取代了阶级矛盾,而且还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用阶级关系替代、掩盖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使文学作品成了图解和宣传阶级斗争的教材。经典阶级斗争创作以政治说教者的姿态,对阶级斗争进行简单而夸张的处理,将社会面貌蜕变成阶级斗争的战场,既严重违背了社会现实,也给文学创作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新时期文学既有大量淡化或避开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否定经典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而《白鹿原》则以其宏大的篇幅,较好地完成了对经典阶级斗争的颠覆,为更好地表现阶级斗争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白鹿原的历史变迁是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展现的,小说虽然反映的是一场政治与社会的斗争,但作者始终没有脱离白鹿原的社会历史现实,将传统宗法社会的道德伦理和农业经济社会的阶级矛盾巧妙地糅合在这场斗争中,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当时特定的社会面貌。
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贫富不太悬殊,经济比较落后,文化非常封建,观念相当传统,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乡村。同村人大多有血缘关系,白、鹿二姓人占多数,这二姓为同宗。村里的穷人与富人的地位往往过不了几代就有换位的。村里的两个成分为地主的首富:一是前辈靠勤劳俭省起家的白嘉轩,一是上代经讨吃要喝发财的鹿子霖;但这两人都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省吃俭用、勤劳起家的地主;同样,也有一些贫雇农,其祖上是地主或富农,因自己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而沦为穷人的。《白鹿原》的地主和长工的阶级矛盾并不很尖锐。白嘉轩和鹿三是世交又称兄道弟,鹿三是白家两代长工,有了收成,鹿三马上就能拿到主人给的粮食,丰收了,主人还能多给。地主郭举人对长工不拘小节,活由你干,饭由你吃。这样的地主和恶霸地主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对长工而言,两者相比,前者便成了好人。我们不能因此说长工的这种认识,是丧失了阶级立场而敌我不分,也不能简单认定这样的地主是假慈悲,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阶级社会里的阶级关系,总是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阶级矛盾可以呈对立状态也可以呈调和状态,只有对立状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演化为阶级斗争。而且,阶级矛盾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域环境不同,表现的状态或形式也不尽相同。动辄将阶级矛盾夸张成阶级斗争的宣传只能是反历史反社会的政治煽动。地主剥削长工呈现的是阶级关系,地主是否尊重、善待长工体现的是地主的道德品质。无论是哪个阶级的全体成员,如用道德标准衡量,其中都有高下之分。文学作品中的经典阶级斗争创作模式,把所有地主都描绘成不是恶霸也是人面兽心,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程式化的所谓艺术处理,不仅违背了客观现实,也破坏了艺术的丰富性。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中,显然表现了对经典阶级斗争创作模式的不屑。
表现经典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对革命或反革命阵营中成员的描写大多流于模式化。道德品质,经济地位,家庭出身等成了塑造革命或反革命人物的基本依据。革命者往往是道德品质的优良者而反革命者通常是道德品质的低劣者;经济地位高的剥削者定是反革命者,这是置革命导师恩格斯于不顾;剥削者家庭出身者如要成为革命者就得像《红岩》里的刘志扬必须经受革命的检验,这是视革命领袖毛泽东于不见。如果说组织对个人的考验是需要的,那么《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就经受了革命组织的反复考验,但历史上根正苗红的中共领袖向忠发就不需要考验了?由于想改变贫困生存环境而参加革命的,其动机一般总比较简单;而身处富裕生存环境而参加革命的,其动机一般则比较深刻;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广东海陆丰共产党人彭湃的事迹足可证明。因此,一切以阶级成分或阶级出身来判断某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的做法是不全面的、不科学的。将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方法引入文学作品创作之中,文学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反历史、反现实的政治工具。《白鹿原》刻意颠覆经典阶级斗争,力求回归历史现实的本来面目,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拨乱反正。
《白鹿原》中的革命者虽有被剥削阶级的,而作者刻意塑造的则是几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者。鹿兆鹏是反革命人物鹿子霖的大儿子,却又是白鹿原的共产党组织最高领导,后又成了解放军的指挥员。白嘉轩的女儿,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白灵,当初则是个国民党员。白嘉轩的大儿子白孝文曾经堕落过,抽过烟土,又担任过反革命武装保安团的营长,最后成为共产党的滋水县县长。这些艺术上的结局在客观上还是具有真实性的,对经典阶级斗争作了强有力的颠覆。但小说对鹿兆鹏参加革命的动机和过程缺乏必要的交代和铺垫,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写实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深刻性。白灵参加国民党仅是因为男友鹿兆海参加共产党而作的随意性选择,后来又让俩人换了身份,白灵改入了共产党而鹿兆海改入了国民党,最终白灵成了革命烈士,鹿兆海也为国民党献了身。但我们不禁要问: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的政治信仰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出身于既得利益阶级的彭湃要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出自于坚定政治信仰,他政治信仰的形成产生于强烈的叛逆精神。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叛逆精神在小说中没有很好体现。我们也许可以理解白灵、鹿兆海两人起初的轻率选择,但后来郑重的转变由于缺乏必要的铺垫,则显得难以令人认同。文学作品固然可追求戏剧性效果,但缺乏必要的逻辑演绎,虽增强了神秘感却减弱了真实性。作者为突出戏剧性效果,反而消解了对经典阶级斗争的颠覆力度,艺术真实被戏说成分所替代,大大减弱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经典阶级斗争无疑是经过粉饰的、矫揉造作的人造状态,现实世界的阶级斗争并不似经典阶级斗争那么纯粹、那么清晰,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矛盾,而是纠缠于复杂的社会发展运动中,是一种特殊的阶级矛盾。《白鹿原》中的社会矛盾展现在宗法社会和政治社会的两个层面上,而阶级斗争主要在政治社会层面上展开,宗法社会层面上展开的主要是白、鹿两家的斗争,本质是族权之争、财富之争,如一定要用阶级分析法,只能是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小说中的鹿子霖实际是想通过政治社会权力组织与传统宗法社会的掌门人白嘉轩抗衡,来维护和巩固自己在白鹿原的地位,就这样他成了政治上的地主阶级代表。在政治上,鹿、白两人只是分别代表了地主阶级中的“执政者”和“在野者”。小说颠覆经典阶级斗争的内容足以令我们作深层的思考,对认识当今中国的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不无启迪,给新时期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流。
陈忠实在新时期文学中,为努力颠覆经典阶级斗争、回归阶级斗争本真作了必要的、有益的尝试,具有开创性意义。但“真正的‘现实主义’,是需要现实的勇气和历史的深度双重的合一”[5]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佼佼者的创作,颠覆经典阶级斗争用力有余,而回归真实阶级斗争着意不足;作为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的作者,现实的勇气有余,而对历史的深度的理解不够。《白鹿原》与《青春之歌》、《三家巷》相比,在描绘阶级斗争时,则不免显得过于简单、粗糙。小说没有把阶级斗争的描述重点放在宗法社会层面上,而放在了政治社会层面上;政治社会的阶级斗争一般比较简单,而要真实地描绘宗法社会的阶级斗争,无疑远比周立波《暴风骤雨》中表现的阶级斗争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面貌,就现实主义作品而言,描述的简单常常会造成表现的肤浅,而描述的复杂往往会造就表现的深刻。《白鹿原》中的政治革命斗争如能与宗法社会内的阶级斗争有机结合,描述出白鹿原上独有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形态,借以展示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才有可能形成作者对阶级斗争的个性化理解,给我们提供独到的审美价值。显然,由于作者没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些,所以在作颠覆经典阶级斗争、回归阶级斗争本真的努力时,就暴露出机智的不够和力量的不足,最终导致了作品在描述阶级斗争时流于一般化、简单化、浅显化。无论是穿越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阶级斗争表现模式,还是穿越现实世界中的本真阶级斗争的表现形态,《白鹿原》都面临了失败。我们不得不说,这部长篇小说只能是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生存性作品”,而没能达到具备独特审美价值的“存在性作品”的艺术水平。
在描绘阶级斗争时,长篇小说《白鹿原》并没有完全建立起作者对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客观的尊重与主观的理解,从而上升到哲学高度,建立起作者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因而无法穿越由政治文化所构成的现实,建立起具有个性化理解的文学世界,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文学功能。
4.结语
《白鹿原》就“寻找”而言是成功的,陈忠实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寻到了与当代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根”。为新时期文学如何寻根,如何表现阶级斗争作了开创性的有成就的尝试。但正如吴炫所言:“‘寻找’的姿态不是一种文学的姿态,文学的姿态应该‘穿越’所寻到的内容,无论是现实性内容,还是原始文化内容,抑或西方哲学与文学观念,去贡献自己对这些内容的独特理解,然后派生出我们独特的现代性创作方法以区别于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方法。”[6]新时期文学应该突破寻找、回归和守望的重围,从而达到穿越、创新和前瞻境界;挣脱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羁绊,从而自觉建设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文化。现实主义作品《白鹿原》在构筑传统宗法社会,颠覆经典阶级斗争两方面基本完成了寻找的任务,但小说展现的传统宗法社会面貌和描述的阶级斗争形态,满足于作“民族的秘史”的阐述和戏剧性效果的追求;没有将宗法社会的构筑与阶级斗争的阐述有机结合起来,没有真正做到在尊重文化现实的前提下,穿越政治文化现实与世俗文化现实,对文化现实进行创造性整合,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就穿越而言是失败的。
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建立一个与现实世界并立的文学世界,为人们提供独特的审美价值。司马长风说:“如果,我们不甘处于在被世界文坛冷落、漠视的姿态,我们必须深长反省。”[7]中国当代作家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作家相比,同样占有厚重的历史、发展的现实、丰富的文化、辉煌的文明,甚至占有的还要多还要好。他们虽在感受、体验和表达上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但在世界观、道德观、文学观上则无自己独到的超越前人与他人看法,创作的多是“生存性作品”,而缺乏如《红楼梦》那样的“存在性作品”。我们期盼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能突破既定的文学与文化世界,穿越传统或西方的思想,有自己的世界观,能构筑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文学世界,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占据自己应有的席位。
引用文献
[1]吴炫:《文化寻根文学及热点作品局限评述之一》,《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页。
[3]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4]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328页。
[5]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40页。
[6]张伟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76、77页。
[7]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