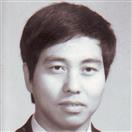比拟作为修辞格,在写作实践中使用的频度是比较高的。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将比拟分作两类:一是以人拟物,称作拟物;二是以物拟人,称为拟人。随着修辞研究的深入,人们注意到比拟还有第三类:以物拟物,即以此物拟作彼物。这三类都已为修辞学界和语文教学界所认同。那么,是否还有第四类:以人拟人呢?
一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比拟的语言形式特点(简称语形特点)。比拟由本体(即被拟体)、拟体(即客体)和拟词(即表摹拟的词语)三要素构成。比拟的语言形式是用拟词将本体虚拟成拟体,本体与拟词必须显现,拟体则往往隐含其中。请看以下三例:
(1)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
侄儿宏儿。
(鲁迅《故乡》)
(2)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朱自清《春》)
(3)老支书直截了当地下达了任务:“让你带一队人马把黑龙潭的水牵到山
下的坝子里来。”
(刘白羽《红玛瑙》)
例(1)中的“宏儿”是本体,“飞”是拟词,拟体“鸟”则隐含其中。这是以人拟物。例(2)中的“小草”是本体,“偷偷”是拟词,拟体“人”便隐匿起来了。这是以物拟人。例(3)中的本体是“水”,拟词是“牵”,拟体“牲畜”就隐藏于句中了。这是以物拟物。
刘大为在《比喻·近喻·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中说:“比拟、移就等辞格中,介体(即本文所说的拟体)是隐含着的”。[2](p34)一般修辞学理论都认为,以物拟人的语言形式是见物不见人,以人拟物的语言形式是见人不见物,以物拟物的语言形式是见此物不见彼物。其实,也有拟体显现的比拟。例如:
(4)列宁笑着说:“我有向导,是您的蜜蜂把我领到这儿来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蜜蜂引路》)
(5)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做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
属梯子。
(徐迟《歌德巴赫猜想》)
例(4)中的“向导”是拟体,指的是人;“蜜蜂”是本体;“领”是拟词。是以物拟人。例(5)中的“尼龙绳子”、“金属梯子”都是拟体,“失败”是本体,“接”、“焊”都是拟词。可见,拟体的出现并不妨害比拟的成立。
另外,比拟中所说的物,其概念是极其宽泛的,整体人之外的一切指称皆是物,包括了所有的具体实物、抽象事物以及非整体人的指称等。例如:
(6)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而不是美国
的民意。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7)于是他晃了晃脑袋,甩掉那些落在他脸上的目光,又不顾一切地向前跑
去……
(陈祖芬《时势和英雄》)
(8)……杂乱的短发便在沙发上鲁莽的摇了几下。
(丁玲《梦珂》)
例(6)中的本体“民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抽象事物,“强奸”是拟词,“女性”是隐匿的拟体。是以物拟人。例(7)、例(8)中的本体“目光”、“短发”,都是非整体人的指称,“甩”、“落”和“鲁莽”是拟词,“水”和“人”是隐藏的拟体。例(7)是以物拟物,例(8)是以物拟人。
由此可见,比拟三要素是构成这种辞格的语形特点。比拟语言形式中的“拟体”虽然一般情况下是不出现的,但是不能完全排除出现的可能。比拟所谓的物的概念虽然是比较宽泛的,但是绝非哲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
接下来,再看符合比拟语言形式特点的以人拟人现象到底有没有。
二
冰心的短篇小说《分》写了一个新生婴儿的见闻。作者把主人公写成了一个年龄上处于婴儿状态,而心智却已与成年人(或大孩子)无异的人物。其中写道:
(9)我羞怯地轻轻的说“好呀,小朋友。”他也谦和的说:“小朋友好呀。”
这时我们已经被放在相挨的两个小筐床里,护士们都走了。
(冰心《分》)
这是“我”与另一个婴儿“他”的语言交流。文中的“我”会“羞怯”,能“轻轻的说”出问候语,能知道“我们”“被放”的是“小筐床”,走了的是“护士”;同样“他”也会“谦和”,也能回应“说”问候语。“我”、“他”和“我们”成了本体,拟体则是隐匿的“大孩子”,而“羞怯”、“谦和”、“说”及说出的话语都是拟词。在冰心这篇小说中,婴儿是叙述者,全篇以婴儿拟作成人,这与拟人体的童话通篇以物拟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络版2003年第12期的《健康准妈妈》上有一篇科普读物,以胎儿为叙述者,描述了胎儿从形成、成长直到出生的整个过程。描述胎儿形成的第一个月的情形时,这样写道:
(10)我只知道,三胚层将来会长成我身体的不同部分,作为“成长核心”。
(鱼淼淼《小胎儿的独白》)
胎儿“我”是本体,“知道”及关于胚胎的知识都是拟词,隐藏的拟体是掌握生育常识的“成人”。胎儿孕育知识恐怕连一些成人也未必清楚地知道,将胎儿拟作生育知识的传播者,无疑起到了令读者倍感亲切的效果。
流传在湖北咸宁的楠竹起源的传说中,也有将胎儿拟作成人,甚至有与人对话的内容。其中这样写道:
(11)忽然听媳妇肚中的胎儿说了话:“不是我不愿意出生,实在是没有到
时候。等到有白马从我们家门口过的那天,你们告诉我,我一定出来。”
(《关于楠竹起源的传说·传说三:楠竹为什么只长在山上》)
胎儿在文中并非叙述者,本体是“胎儿”,“说”及说话的内容都是拟词,隐含的拟体是“成人”(或大孩子)。胎儿这番话全是成人语,而且其出生完全不受生育规律的约束。体现了传说故事的趣味性。
将胎儿、婴儿拟作成人(或大孩子)的语言形式,符合比拟的三要素结构,这是以人拟人,即以小人拟大人。
除了以幼者拟作长者的语言现象外,还有以死者拟作生者的语言现象。例如:
(12)他对于自己的死,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不治之症,有什么办法呢?
(周克芹《断代》)
(13)那么我提醒你们:我死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骇人的阴谋,极可能瓦解
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
(12)、(13)两例都出自小说。两例中的第三人称“他”和第一人称“我”皆是死者,但他们却跨越了生死界限,有了心理活动,有了说话能力,能对生者表达“遗憾”抒发感叹:“不治之症,有什么办法呢?”会对生者进行“提醒”引发思考:“我死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骇人的阴谋,极可能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其中的“我”、“你”等死者是本体,“遗憾”及遗憾话语和“提醒”及提醒内容,都属于拟词,隐含的拟体则是生者。
悼念文章里,也有以死者拟生者的现象。2006年6月16日的《文汇报》上,有篇文章这样写道:
(14)严文井走了以后,我有一次忽然想起,他现在走到哪儿了呢?于是,我
问他。他说:“我这个人最不擅长记地名,这个地方叫什么,我无法答复。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它是一个人人都不喜欢,人人都不愿意来,可人人最后都必定会来
的那个地方。”
(康志强《文井,你现在走到哪儿了》)
这篇写实的应用文与虚构的文艺小说一样,让死者“他”与生者“我”,跨越了生死界限,进行对话。作古的严文井先生竟能“说”出这番充满哲理的话。严文井先生显然被拟成生者了,他的“说”及所说话语,就属拟词了。
再看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七哀》诗和清代大学士纪昀一则笔记小说的摘句:
(15)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
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
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
(阮瑀《七哀》)
(16)髑髅作泣声曰:“君气亦盛,故我不敢祟,徒以虚词恫喝也。……”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
上述两例中的“精魂”、“髑髅”与(7)例中的“目光”和例(8)中的“短发”不同,后两者不能用“人”来替代,前两者则均可用“死人”替代。再看一例:
(17)多少颗年轻的心,长起翅膀飞向南方。
(李季《最高奖赏》)
例(17)里的本体“心”,即使没有“年轻”作定语,也不能作物理解,只能是“人”的借代。“精魂”与“髑髅”,也实为死者的借代。因此,(15)、(16)两例都是将死者拟作生者。例(15)中,死者的“出”、“望”和“见”;例(16)里,死者的“泣”、“曰”及所言,皆是拟词。
将死者或死者的借代:精魂、髑髅,拟作生者的语言形式,也符合比拟的三要素结构。但视胎儿、婴儿为人容易认同,而对死者也许不易认同,现在,试作分析以便认同。首先,以“物质不灭”的哲学观来看待死者,将死者当作物,如同把精魂、髑髅说成是迷信产物一样,终究不妥;其次,物既然有具体、抽象之别,人何妨有生、死之别;最后,如果把以幼拟长归为以人拟人类,而将以死拟生单作一类,就不免失之琐碎。因此,死人拟活人,也作以人拟人。
三
比拟既有外在的语形特点,还有内在的语言意义特点(简称语义特点)。排比、对偶、反复、设问和反问等辞格的修辞效果主要取决于语形特点,而比拟、夸张、移就、比喻和通感等辞格的修辞效果主要取决于语义特点。因此,弄清比拟的语义特点,对确认以人拟人更为重要。
比拟是通过本体与拟词的组接,从而造成语义的蒙太奇效果的;在强制性的组接下,本体接受拟词的表述就被异化为拟体。要达到异化效果,本体与拟体必须有差异。现有的修辞学理论认为,本体与拟体应是不同范畴的两种事物。史封尘说:“用人比拟人或用物比拟物,都是违反比拟差异性规律的。”[8](p47)这种说法已被以物拟物的认同所否定。人与物距离固然甚远,物与物距离也很远,因为它们分属不同的物种。刘大为说:“成为介体词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它的所指对象与本体必须是距离甚远的两类不同事物,其次在一定的语境中它与本体词形成了某种语义联系。”[2](p35)幼者与长者、死者与生者,虽同属人类,差距也是很远的。
本体与拟体的距离,是通过拟词来体现的。拟词呈现的是拟体的可能性特征,换言之,也是本体的不可能特征。例如:
(18)可是急人得很,山头上忽然漫起好大的云雾,又浓又湿,悄悄挤进门
缝来,落到枕头边上,我还听见零零星星几滴雨声。
(杨朔《泰山极顶》)
(19)四月里胡宗南占绥德,不是说:“天上飞机忽隆隆响,洋面撩到飞机场”
吗?他们占了三天,不是夹着尾巴跑了?
(柳青《铜墙铁壁》)
(20)战火闪烁,战鼓雷鸣,人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我们英雄战斗的年代。
(刘白羽《红玛瑙》)
例(18)中的“挤”是“人”的可能性特征,是“云雾”的不可能性特征,形成以物拟人。例(19)中的“夹着尾巴跑”是“动物”的可能性特征,是“人”的不可能性特征,形成以人拟物。例(20)中的“染红”是“织物”的可能性特征,是“年代”的不可能性特征,形成以物拟物。同样,长者、生者的所思、所感、所行、所言,对幼者、死者而言就是不可能性特征。例如:
(21)我还会在每年的清明复活一次。
(风起云飞《我的葬礼谁在哭》)
(22)王妃为其喂奶时,婴儿说:“我乃化身瑜伽女,……阿耶!”
(迦那伽罗《佛母益西措嘉略传·乘愿降生》)
例(21)中的“我”是死者却有着“复活”的念头,这念想只能是生者的可能性特征,对死者来讲就成了不可能性特征。例(22)中的“婴儿”是幼者竟能“说”,说话能力只能是长者的可能性特征,对幼者来讲就成了不可能性特征。由此可见,比拟的本质不在于本体与拟体两者的种类差距,而在于将拟体的可能性特征变成本体的不可能性特征。
人与物或物与物所构成的比拟都是不同种类事物间的虚拟,而幼者与长者、死者与生者所构成的比拟则是同类事物的不同形态间的虚拟。因此,就不可能性特征而言,似乎也有所不同。前者依赖的是性质上的不可能性特征,而后者好象凭借的是程度上的不可能性特征。现有的修辞学理论一般认为,比拟是将拟体的可能性特征,转化为本体的性质上的不可能性特征所形成的修辞格;夸张则是将被夸体可能性特征,加强为程度上的不可能性特征所形成的修辞格。“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诗句中说白发有“三千丈”,与实际尺寸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灰白如钢丝般的头发,矮壮的身材,一看就是斯大林的后人。”(任秋凌《小斯大林走向俄政坛》)句子中说头发“如钢丝般”是比喻兼夸张,极言头发的硬。头发之硬与钢丝之硬也是程度上的差异。人与物的互拟,以物拟物,拟词所体现的特性对本体来说,显然属不可能性特征。以人拟人的拟词呢?婴儿要长大,拟词所体现的特性对长大后的婴儿而言,就是可能性特征;同样,拟词所体现的特性对死者的生前而言,也是可能性特征。这种对本体而言的不可能性特征,如从历时角度分析,才是程度上的不可能性特征;而从共时角度分析,便是性质上的不可能性特征。这是以人拟人与其它三种比拟关键的不同之处,但这并不妨害以人拟人的成立。
现将以人拟人作为比拟的第四类提出,求教于修辞学界和语文教学界人士。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2]刘大为,比喻·近喻·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王卫兵,现有的比拟理论存在漏洞[J],修辞学习,2004(4).
[4]张志公,修辞概要[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
[5]周翔圣,古文辞格例解[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
[6]李贵如,现代修辞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7]刘焕辉,修辞学纲要(修订本)[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8]史封尘,汉语古今修辞格通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