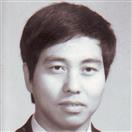《永远的尹雪艳》话剧剧照
序言
上海自开埠以来,一方面与中国传统保持着割舍不断的血缘联系,一方面承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势浸润,成了东西方文化杂交的混血儿。上海独特的城市形象和品格,无论世人如何褒贬臧否,却始终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张力和不尽的诱人魅力。在这东方大都市里,黄浦江水犹醇酒,令人心醉,霞飞路宅如美人,摄人心魄,引无数英雄豪强竞折腰。白先勇童年时在上海只住了二年半,便对上海的繁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写出了以上海为怀旧客体的乡愁佳作——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以下简称《永》)小说中作为怀旧主体的人物活动的现实舞台,虽局限在台北,但通过回顾式的描述,整篇小说却被浓郁的上海物质文化生活气息笼罩着。
双城记的主城
《永》实际上是一部微型的上海和台北的双城记。但是,小说对双城的发生的事情,既非采用对叙也不并重书写。白先勇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关切,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双城的事相隔十几年,因此《永》描述双城的时态是不同的:写上海用的是过去进行时和过去完成时,写台北用的是现在进行时。由于运用了过去进行时,书写上海的容量显得颇大,这对表达作者或小说中人物永远无法排谴的上海不了情起到了强化作用,体现了作者“在于怎么写”的创作理念。
《永》中的城市标识——建筑、场所,突现了双城的不同形象和不同品格。上海有:百乐门舞厅、国际饭店、兆丰夜总会、兰心剧院、五香斋、霞飞路的侯门官府、法租界的花园洋房、交通大学等,台北有:鸿翔绸缎庄、小花园、红楼、西门町、三六九里、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仁爱路的高级住宅区等。《永》中提及的城市建筑、场所是作者有意甄选出来的,台北在上海面前确是望尘莫及的。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之高度,绝非西门町、三六九里或红楼所能比及的;霞飞路的侯门官府、法租界的花园洋房之豪华,并非仁爱路的高级住宅区所能企及的;仁爱路的新尹公馆,尹雪艳也只是主观不肯把它降低于霞飞路的老公馆的排场。如果把上海比作皇宫的话,那么台北则是相形见绌的行宫。作者实写的台北只是轻描淡写,而虚写的上海却是重彩浓笔;写台北就是为了反衬上海,写台北就是写上海。
对台北的娱乐、饮食和休闲等生活消费的质量,《永》中的人物总是用上海人的目光、态度和尺子、标准去看待、衡量和评价的。他们在台北三六九里吃桂花汤团时,却津津乐道起上海五香斋的蟹黄面。看红楼的绍兴戏,就是欣赏风靡上海的越剧;食西门町的京沪小吃,就是品尝上海的小吃、点心。尹公馆的上海厨子更是上海饮食的加工制造者。台北的吃喝玩乐的内容只要克隆上海的,他们就满怀兴味;即便如此,这些来自上海的台北人,仍是念念不忘真正上海的吃喝玩乐。他们过着台北的日子,想着上海的生活;看着台北碗中的,惦着上海锅里的;过着台北的日子,想着上海的生活。台北尹公馆是他们心中的上海百乐门,是重温上海的聚会所,在这里可以暂时忘记现实中的台北,回到梦幻中的上海。
这部微型的双城记是以台北的现在进行时态为主线,以上海的过去进行时态和过去完成时态为副线,表达自上海迁居到台北的上流社会男女对老上海的怀旧幽情,在以回忆为基调的《永》中,主线只是配角,而副线却是主角。那些习惯、迷恋上海物质文化生活方式的人们,“身在台北,心在上海”。因此,无论从小说的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部双城记中的双城构成的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主辅关系。上海是《永》中的人们曾经居住过且至今心仪的主城,而台北则是人们无可奈何迁徙而居的辅城。
命运神的大殿
有人称尹雪艳为死神、欲望神和命运神,并以一些人的命运加以诠释。《永》中有“煞星”之说,这是对占有或试图占有尹雪艳的男人而言的。王贵生、徐壮图和洪处长就是其中的代表,不是被克死(前二者)就是被克得丢官破产(后者)。有人说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在尹雪艳这里得到欲望满足的同时,尹雪艳也就将这些人一步步地引向灾难。以上三者便是因肉欲被尹雪艳引向灾难的。当尹雪艳“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战的人们祈祷和祭祀。”时,她又是何神呢?死是命运的终极形态,欲望是命运的激活因子。因此,命运神原本就可司人的生死、欲望等。与其给尹雪艳封多个神衔,不如只给她封一个权位重的神衔:命运神。唯此,才不致搅得神序紊乱,搞得神责交错,弄得神职泛滥。
《永》中写道:“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这句话揭示了尹雪艳的象征义。尹雪艳既然是诠释上海的命运神,那么上海便是命运神的大殿,台北只能是命运神被搬移后的小殿,而《永》中的芸芸众生则是拜倒在命运女神莲花座跟前的善男信女们。出生于苏州的尹雪艳,是在上海羽化为神,她的神性具有海派文化的特征,在台北之所以能继续受到顶礼膜拜,是因为善男信女们都是依恋上海生活的人。尹雪艳之所以不会老,在于她具有海派神性,永远燃着上海牌的香火,能使脱离上海而喜欢上海的男女信徒,在失去中回味失去,在现实的黯淡中延续过去的辉煌,在台北的小殿里朝拜来自上海大殿的命运神,使自己的灵魂得到超生。
白先勇的笔下的尹雪艳是红舞女,又是社交皇后,上海洋场男士们对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儿”,虽心存猥亵的歹意,但也不乏敬畏的诚意。正是这种敬畏塑造了尹雪艳的神格。“尹雪艳有迷男人的工夫,也有迷女人的工夫。”应该说,尹雪艳的神格是双城的善男信女们的人格共同塑造的。尹雪艳无论在上海还是台北,“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令人们陶醉于现实的或过去的上海生活中。尹雪艳是一尊上海之神,上海的魅力就是这位命运神的魔力。她能让善男信女在台北继续享受上海的生活,对她的朝拜其实是对上海物质文化生活的朝拜。“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底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台北是座命运神的小殿,尹公馆就是命运神的莲花座。殿虽小了,座得尽量原汁原味。朝拜者原本应跪在上海这座大殿的团蒲上顶礼膜拜掌命运的神祗的,但命运把他们带到了台北,只能在台北这座小殿里朝拜,祈祷自己的灵魂能永驻上海。
生死魂的栖地
《永》中的芸芸众生基本上都是拜倒在尹雪艳神座下的善男信女。他们的命运线都被尹雪艳牵引着,受着命运神的摆布。王贵生、徐壮图和洪处长,是用钻石玛瑙穿成的链子,企图套在尹雪艳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者。前二者落得命丧双城也没进得温柔乡,后者以妻离子散和十个条件为代价只换得好进景不长的高唐梦。意气风发的上海的绅士以及仕女们,命运乖谬而奔走台北的吴经理、宋太太们都离不开说不尽、道不明的尹雪艳。尤其在台北,尹公馆是旧雨新知的聚会所,尹雪艳是一个最会安抚灵魂的命运神。
尹雪艳是一个象征和代表上海物质文化生活的命运神。如要对她有非分觊觎,便是动摇神位,是没有好下场的,如想得到她的同情、安慰和帮助,只要是不亵渎神灵的,都会得到熨帖的援助,得到援助的同时也就捍卫了神位。双城中的达官贵人及其太太们无论发迹于哪城,之都能被尹雪艳拘到跟前来,表面上是尹雪艳色艺的引诱,实质上是上海文化生活底蕴的诱惑。尹雪艳的姿色只有经过上海文化的熏陶和滋润才能获得令人垂涎的拘人技艺。我们很难设想一个纯粹的苏州女子没有上海的生活经历,会使那些有财、有势、有权的善男信女们拜倒在她的莲花座下。王贵生的死,与其说是为得到尹雪艳而死的,倒不如说是因过于沉溺在纸醉金迷的上海洋场生活而不能自拔而死的。洪处长在上海的妻离子散以及在台北的丢官破产其可悲的命运,也是为纵情享受上海洋场生活和保住上海生活质量所致。发迹于台北的徐壮图也是慕名尹雪艳的色艺,到尹公馆来享受充满浓郁上海气息的生活。徐壮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曾受到上海文化生活的熏陶、上海物质生活的影响,成了台北的实业巨子,财富一多,享受就成了第一要义,怀念上海,重温社会上海的物质文化生活,无疑是他挥之不去的上海情结。徐壮图的直接死因似乎是迷恋尹雪艳导致,而实质是纸醉金迷的上海生活方式要了他的命。那些吴经理、宋太太们离不开尹雪艳,就是离不开上海生活方式。一切拜倒在尹雪艳神座下的善男信女,归根结底他们崇拜的是上海的物质文化生活方式。
双城的朝拜命运神的灵魂们,无论是生的还是死的,他们都将上海作为生魂死魄的栖息地。生死于上海的魂魄自不必说,就是在尹公馆那些感到有“一种宾至如归,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的人,也是将自己的生魂寄托在对上海的不尽的怀念中。他们只是在片刻“乐”的时候,才暂时不思“蜀”,但“乐”是短暂的思“蜀”是恒久远的。尹雪艳称呼人们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这些人如同受过诰命一般,顿时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这就是命运神抚慰生魂的神力。尹雪艳在台北小殿的神力,是在上海大殿修炼而成,没有上海就没有台北的神位。台北的朝拜者无论是新贵还是旧知他们都是身居台北,心系上海的信徒;他们痛苦地忍受着灵肉分离的煎熬,但他们祈祷着“即使肉体腐烂于台北,灵魂也要栖息在上海”的心愿。上海是他们永远想朝拜的大殿。
结言
老上海是一个既可爱又可恨的东方大都市,是冒险家的乐园,可以成全你也可以毁坏你;它充满着挡不住的诱惑,主宰着无数为之竞折腰的英雄豪强。《永》中的尹雪艳是上海的象征,小说中上流社会的芸芸众生对尹雪艳的依赖,表达了他们的对上海生活的体验、理解和看法。白先勇在《永》中,第一句就是:“尹雪艳总也不老。”凡人都得老,只有神不会老,尹雪艳就是神。尹雪艳主宰着那些与上海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者或乡愁者的命运。有了朝拜尹雪艳的善男信女们,才能造就尹雪艳这样的命运神,这与任何造神运动是一样的。尹雪艳能修成正果,固然有她个人的因素,但上海文化生活则是使她修成正果的根本原因。《永》是被公认的怀旧思乡之作,因此,我们在解读《永》时,看到了一群身居台北对故乡无限眷念的上海人,读到了上海独特的城市形象和品格,感到了“永远的上海”这样深沉的象征意义。
二ОО三年三月